
它们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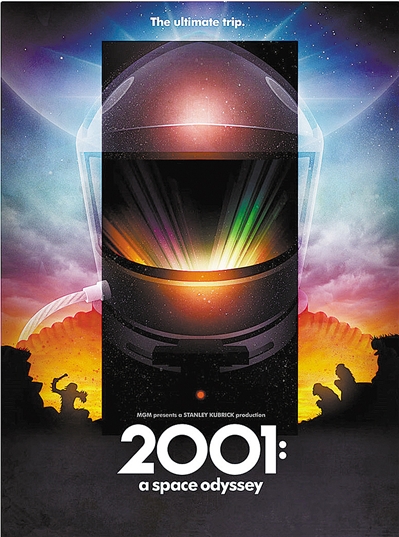
祂们

他们
任 超
即将在大陆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《异星觉醒》中,秉承一贯的不作不死精神,一票科学家将来历不明的火星智能生物细胞带回空间站,予以深情的呵护和培养,希望驯化出一个人类的好朋友。至于结果呢,从电影预告片中可以得知,可谓是愚蠢与凶残齐飞,血肉共残肢一色。
科幻电影中所出现的,具有一定智能的外星生物形象,几乎与电影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。以1902年梅里爱的《月球旅行记》中的“月人”为滥觞,此类形象可谓不可计数。究其本质,马克思对于宗教的伟大论断同样适用:“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,在这种反映中,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”。
这些外星智能生物,其实只是“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”的,对于人类心灵的映射罢了。由此,套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,其可以被粗略地分为“映射本我的外星智能生物”“映射自我的外星智能生物”和“映射超我的外星智能生物”三大类。
“本我外星智能生物”,是那些低等、偏执不可理喻的外星敌人,它们映射着纯然的本能和欲望,代表了人格中动物性的方面。它们是人类的对立者,是人类潜意识中的恐惧的外化。
其中最为典型的,就是《星河战队》系列电影中的虫族。它们生活在贫瘠荒凉的星球,受制于低等野蛮的社会形态,嗜血好战的同时,几乎毫无科学技术可言,除了“心灵控制”“电浆喷射”和“小行星攻击”等莫名其妙的巫术一样的手段,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武器,就是赤膊上阵血肉相拼的“虫海战术”。
在海因莱因本人编剧的这部划时代的作品中,即便不谈意识形态色彩,虫族在各个方面上,也是作为联邦公民所具有的完美人格的对立面而存在的。说得更遥远一些,虫族所反映的,是深藏于智人的潜意识中,对于十万年前东非大草原上各类致命昆虫刻骨铭心的恐惧和仇恨。
“自我外星智能生物”,是那些在心智和文明程度上,与人类比较接近的外星生物,它们映射着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,代表了人格中社会性的方面。他们是我们的镜像,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奇幻式表述。他们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“外星人”,在科幻电影中的数量最为众多。可以再细分为三种。
第一种,可以称其为“邪恶敌对者”。包括那些科技程度也许较人类更高,但心智和文明程度却未必,与人类作对的敌人。例如《星际之门》中假冒太阳神“拉”的外星人,空有毁天灭日的技术手段,而不能推行仁政,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毁灭;而《独立日》中的外星人,也是虽然掌握可以跨越星系的高级科技,却不能接受和谐共存的简单观念,必要将人类赶尽杀绝而后快,同样也招致了自身的失败。顺便说一句,这两部电影都出自导演艾默里奇之手,这样的设置,恐怕并非仅仅是偶然。
第二种,可以称其为“中性的共存者”。指的是那些与我们一样,善恶兼备,复杂多变,如同我们的影子,甚至就生活在我们身边,成为了人类社会一部分的共存者。例如《黑衣人》中形形色色的外星定居者,《第九区》中的难民种族龙虾人,正是暗喻了移民社会及其现实而复杂的问题,几乎可以被称作是现实主义作品了。而在《黑衣人》的最后段落,当邪恶大反派现出本体原型的时候,从本文的分类法的角度看来,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:邪恶如它,终究还是必须成为一只大虫子。
第三种,可以称其为“善意的引领者”。他们在各个层面上,向我们展示着世界应该成为的,更好的样子,试图引领我们走向乌托邦,或者说至少是更光明一些的未来的善意的外星人。电影中的这个群体非常巨大,可谓不可胜数。例如《第三类接触》中为和平而来的星际音乐家,《ET:外星人》中外形和内心形成极大反差的童年挚爱(也许《银河护卫队2》中德拉克斯眼中的螳螂女就是这幅形象?),《深渊》中被爱感动而取消毁灭人类计划的发光外星人,《阿凡达》中与自然母亲融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之光那威人,《降临》中看穿一切依然跨越时空赶来营救人类的七肢桶,《童年的终结》中为人类带来科技和繁荣,受命引导人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的监护种族卡瑞纳人等等。
“超我外星智能生物”,从伦理学、社会学甚至是物理学角度上看来,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,映射着超我的神性,代表了人格中道德理想的方面。祂们可以说是引领者的升级版本,是终极的掌控者,是心灵的本原,是我们所追寻的神性的载体,祂们就是“道”本身。
例如《2001:太空漫游》中人类进化下一个阶段的能量生命形态,《童年的终结》中宇宙智能生物进化终极的宇宙精神合一体,都是祂们的体现。这类形象在科幻电影中并不多见,上述例子也是同出于克拉克的笔下。
究其根源,也许正是因为过于接近宗教和神学,远离了一般观众的审美接受习惯。诚然,先进的科技在起初都很像巫术,但是如果因此就放心大胆地把一切巫术都阐述为先进的科技,未免失其路径。当观众坐在电影院里,看着银幕上的一束光芒席卷宇宙的时候,两种解释比较起来,“这是大爆炸,是宇宙的开端”和“这是柏拉图所说的宇宙灵魂的开端”,我们不得不承认,还是前者更像一部科幻片。
 相关推荐
相关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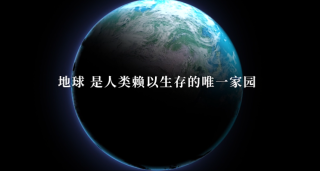

 渝公网安备 50019002502348号
渝公网安备 50019002502348号